桌子与花果
——关于哲学问题的“奇思妙想”
李顺亮
2017年1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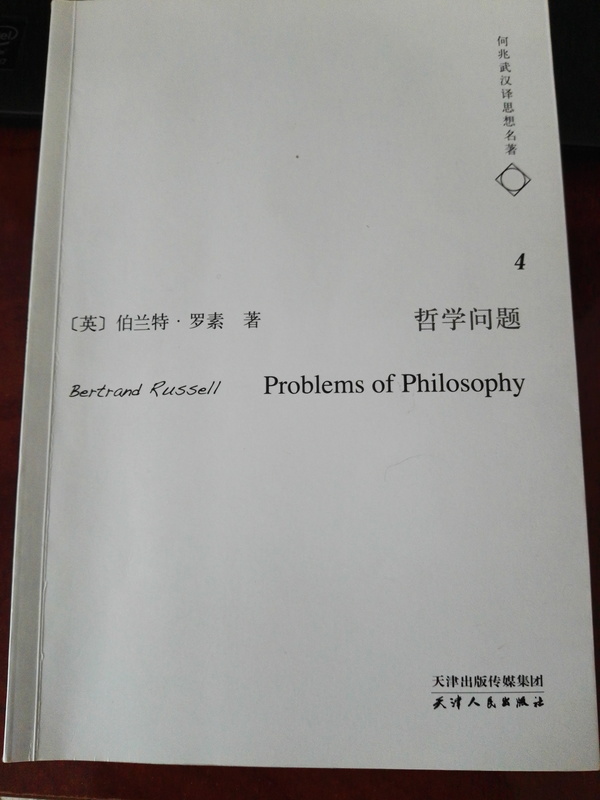
哲学问题在罗素看来,是桌子问题。但在我看来,是花的问题,也是果的问题,更是有什么花结什么果的问题。世界的花无数,世界的果亦无数,但真理只有一个,即:有什么花结什么果。
2014年10月,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兆武汉译思想名著,收录了1910年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下的著名哲学导论——《哲学问题》(Problems of Philosophy)。在导言之中,约翰·斯科鲁普斯基说:“罗素称它是他的‘廉价本的惊险小说’。”其实,罗素在书中破解的是重大的哲学基本问题。而“惊险”之处恰恰在于,这是由一张怎么看都平淡无奇的桌子,所引发出来的奇险无比的哲学旅行,并且让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惟有随之起舞,跟着他的思绪起起伏伏。
生活之中,桌子无处不在。问题是,突然间,我们在哲学家的引导之下发现,桌子居然不是桌子本身,这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也是十分让人震惊的。原来,桌子仅仅是我们的感觉材料之上感觉出来的东西。于是,关于桌子的奇思妙想纷纷出笼。哲学第一次不再高大上,而是如此平凡,甚至平凡到有些无聊,连一张桌子都要七嘴八舌争个不休。但是,正是这样看似盲人摸象般的“滑稽”,让哲学不仅接上了地气,而且步步在争论中推向深入,使我们的心灵和“上帝”的心灵渐渐相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上帝的科学。而这是的“上帝”,在中国用“道”来表述,其实显得更为准确和生动一些。于是,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宇宙的整体综合,上帝的心灵就是宇宙的道。而道在上善若水之中,同样也在一张桌子之中。道分阴阳与黑白,可化万物。道并不玄乎,是我们生活日常之中可以感知的存在。同样,上帝也并不玄乎,只不过是西方之人换了一个名词来表达他们的心灵世界。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并不仅属于西方,东方亦有东方的哲学。因为东方的桌子,一样是现象与实在的矛盾统一体。只不过,东方的道是可以直击心灵的禅悟,而西方的上帝却在西哲们的争论之中纠结,究竟我是我吗?“也许根本就没有桌子。”也许,也根本就没有上帝。我是我,我又不是我,正如道之阴阳两面。
“要想做一个哲学家就必须锻炼得不怕荒谬。”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先贤大哲也殊途同归。庄子甚至因之而颠狂,以致后来研究他的刘文典,也因庄子之学而成了狷介狂人。毕竟,要想真正懂得庄子,就得和庄子心灵相通,不外狂无以为内知。关于桌子,西方哲人的奇思妙想也是够荒谬的:“莱布尼茨告诉我们,它是一堆灵魂;贝克莱告诉我们,它是上帝心灵中的一个观念;严谨的科学几乎也同样使人惊异地告诉我们说,它是极其庞大的一堆激烈运动着的电荷。”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必须承认,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在我们自身之外和我们经验之外的那些事物的存在。世界是由我自己、我的思想、感情和感觉所组成的,其余一切都纯属玄想……”于是,不管是桌子,还是什么,还是什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荒谬的问题,似乎瞬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思想本身。这不就是“我思故我在”吗?也正因为每一个“我”不同,所以每一个“在”也是有别的。因此,“在不同的人的个人空间里,同一客体仿佛具有不同的形状……”千变万化,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世界之奇妙正在于此。
空间如果加上时间,这个世界就变得更为复杂。在时间面前,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存在,都是真正的不在。在与不在,其实都是时间的次序决定的,此在而彼不在,甚至可以说:万物都在,又都不在。“当我们说事件所仿佛具有的时间次序和它们所实在具有的时间次序是相同的,我们这里必须防范一种可能的误解。绝不能设想,不同的物体的不同状态与构成对于这些客体的知觉的那些感觉材料有着同样的时间次序。”在中国的神话世界里,也可以看出对于时间次序的一些固有思维惯性。雷公和裂缺是同时出场的,但二神执行任务的次序是不同的,裂缺先打闪电,雷公再打响惊雷。
不管是空间,还是时间,不管是空间的位置,还是时间的次序,都要我们用心去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一切存在的,或者至少,一切为人所知道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都必然是精神的。”唯心主义虽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待唯心主义,正如说它一声荒谬那么简单,那就大错特错了。“不习惯于哲学思考的人,可能易于把这样一种学说看成是显然荒谬的而加以抹杀。”那么,我们就忘了:“自觉是人之异于禽兽者之一端。”人虽然与禽兽有别,但是人并不会比禽兽高明到哪里去,往往会犯同样的错误。
“每天喂小鸡喂了它一辈子的那个人,临了却可以绞断这只小鸡的脖子……”习惯,导致无须判断,以致“判断”失误。习惯,造成了判断的缺位。这样的例子,对于人而言,同样比比皆是。“我们所处的地位并不比脖子出乎预料被绞断的小鸡更好些。”于是,要经验,还是要理性,就成了问题。而“经验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两派之间的争论,曾经是哲学史上的大争论之一。前者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得来的”,而后者认为“还有某些我们不是凭经验而知道的‘内在观念’和‘内在原则’。”
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普遍性,而经验其实都具有特殊性,如果因为经验而以为必然生出先验,便是如小鸡般自寻死路。但是,哲学理论就在不安之中否定,在惶惑之中前行。而否定之否定,让哲学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最初那个否定的原点。在理性主义者的传统中受教育的康德,对于休谟的哲思是惶惑不安的,而站在从休谟到康德以来所有哲人肩膀之上的罗素,则是充满自信的:任何哲学问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当我们判断2加2等于4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对于我们的思想作出一个判断,我们所判断的乃是所有实际的或可能的对对成双。”世间万物及其关系,都可以用数及其数学加以表达。而蕴涵于世间万物及其关系之中的哲学,既如数般实在,又如数学一样玄妙。用中国的道家理论其实一解就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一是什么,一双是阴阳的合体,即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天与地。
每一位哲学家的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其实也就是存于天地万物之间的道。“对于柏拉图来说,真正实在的世界就是理念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超感觉的世界,是脱离感觉世界的真正的存在。它是普遍,而不是特殊的。公道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不是特殊的,所以它本身便不能存在于感觉世界之中。并且它也不像感觉的事物那样变化无常;它本身是永恒不变的、不朽的。”而人作为个体之所以会消亡,正因为他是个体的,亦即特殊的。
于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共相不是思想,尽管它们是在作为思想的客体的时候才为人所认识。”各自有各自的“白”,即殊相之“白”,但每个人思考“白”的行为,又具有共性特点。这种共性特点的“白”,就是共相,是你我不同之“白”成为可以沟通的相同之“白”的重要原因,也是坚实的基础。“思想和感情、心灵和物质客体,都是存在的。但是共相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存在着;我们要说,它们是永恒的,或者说,它们具有着实在,在这里,‘实在’是超时间的,是和‘存在’相对立的。”“存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昙花一现的,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即都是“不存在”的。这正是正反合,一个中国传统古老智慧的结晶,所谓阴阳合一之中的阴阳互转,正是最好的例证,也是最妙的解释。
认识殊相,凭感觉就好,而认知共相,就需要智慧。“当我们看见一块白东西的时候,最初我们所认识的是这块个别的东西;但是看见许多块白东西以后,我们便毫不费力地学会了把它们共同具有的那个‘白’抽象出来……”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而要认知共相,还需要我们有归纳之后的抽象能力。归纳之后的抽象,远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相对而言,抽象能力的大小,与一个人的聪明程度成正比。“通常我们是通过特殊事例才能明了普遍原则。不需要事例的帮助便能随时把握普遍原则的,这是只有习惯于处理抽象化的人们才能做得到的。”抽象能力是人的能力,而不是猪或者其它动物的能力。因此,抽象能力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人之所以为人,是因其有抽象能力,而不像动物只有低层次的感知能力。
今天,很多人都感叹于科学的强大,很少有人认识到科学的渺小。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学上的概括,也因此有了日益宽广的归纳基础。“这虽然使得确切可靠的程度大一些,然而它所提供的性质并没有差异:基本的根据还是归纳的,也就是从事例而来的,而不是先验的,不是和属于逻辑与算术中那种共相有关的。”哲学虽然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且是科学突变的思想基础。但是,科学的进步,其实只对科学本身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哲学是多少有些无能为力的。问题是,一般的人并不能够看到这一点。这也正是为什么千奇百怪的哲学流派,甚至从远古而来的某些哲学流派,仍然能够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广泛存在的原因所在。
“许多人都觉得,一种没有理由可加以说明的信仰就是不合理的信仰。”其实,信仰没有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信仰只有信与不信的问题。每个人都固执地信着自己的信仰,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一旦这个信仰轰然倒塌,无论是因为自省还是外力造成的,都会让人难以接受。于是,就不得不自己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重建自己的信仰。否则,便只有痛苦与煎熬。当然,重建信仰的过程,也可能是向上升华或者向下堕落的过程,各因机缘而各有收获。
信仰是与真理直接相关的东西,谁都认为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真理。究竟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妄,其实只有上帝知道。问题在于,没有虚妄,也就没有真理。如同硬币,必定要有正反面。没有正面,就没有反面存在;而没有反面,同样没有正面存在。只有正反面合二为一,即合体,硬币才是真实的。这就是阴阳必然合而为一的同时存在,所谓的正反合。阴阳只可能互转,但绝不可能最终取代。取代就意味着“不在”,即消亡。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理解了罗素关于真理的理论:“(1)它许可真理有一个反面,即虚妄,(2)把真理作为是信念的一种性质,但(3)使真理的性质完全有赖于信念对于外界事物的关系。”
“心灵并不创造真理,也不创造虚妄。它们创造信念,但是信念一经创造出来,心灵便不能使它们成为真实的或成为虚妄的了……”于是,“当一个真确的信念是从一个虚妄的信念演绎出来的时候,便不是知识。”“但是事实上,‘知识’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它和‘或然性意见’是混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了:“我们一切的真理知识都带有几分存疑的程度,一种理论只要忽略了这个事实,显然它就是错误的。”问题是,绝大部分人并不愿意或不能直面这一点,都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或者要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科学探索无限,哲学永无止境。“倘使我们在一条线段上取两个点,不论这两点间的距离如何之小,显然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别的点;每一距离都可以分成两半,这两半又都可以再分成两半,这样便可以无限地二分下去。”对此,庄子早有形象的说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人类智慧的胜利在于:“想用先验的原则来给宇宙加以规范的企图已经破了产。逻辑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各种可能性的阻碍,而是成为了人们想象力的伟大解放者……”“哲学的根本特点便是批判”,“然而当我们说哲学是一种批判的知识的时候,必须加上一定的界限。倘使我们采取完全怀疑者的态度,把自身完全置于一切知识之外,而又从这个立场来要求必须回到知识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便是在要求不可能的事,而我们的怀疑主义也就永远不会被人所驳倒了。”这样的例证也很容易找到,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正是因为没有界线,而不可取。
一个学科的存在,与其不断向前推衍,和这个学科有没有实用价值,其实是无关的。“哲学的价值大部分须在它那极其不确定性之中去追求。”而“哲学的用处在于能够指点出众所不怀疑的各种可能性。”“现在所以要推荐研究物理科学,与其说是根本原因在于它对学生的影响,不如说是在于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这种实用性是哲学所没有的。”历史学同样如此,并没有多少实用性。但是,有一点是历史学与哲学之间共通的:“只有在心灵的食粮之中才能够找到哲学的价值;也只有不漠视心灵食粮的人,才相信研究哲学并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世界有这样的桌子,有那样的桌子。有万种花,亦有万种果。万花筒里的世界是最美的,因为道全在你的一手掌控之中。“……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实实在在,心灵便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哲学让我们眼中的世界更美,也让我们自己活得更真。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一回多少有些荒谬的“奇思妙想”吧!
| 关于丝路 | 丝路网史 | 版权声明 | 法律顾问 | 联系我们 |
Copyright © 2004-2023 by onesl.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建议您使用1024*768分辨率、火狐浏览器浏览
